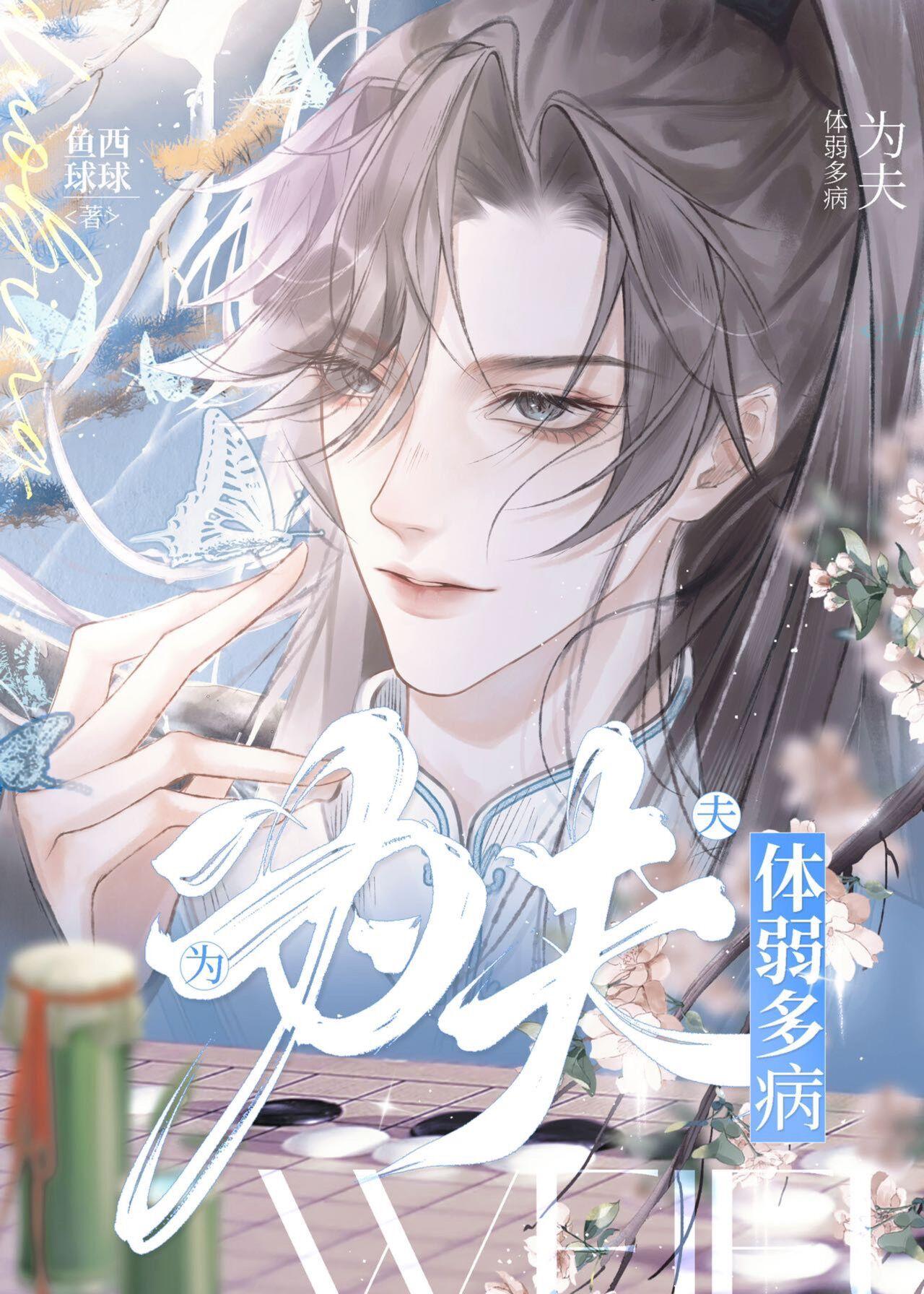千千文学网>九龙夺嫡,我真不想当太子 > 第一百七十七章 步步惊心处处都是陷阱(第1页)
第一百七十七章 步步惊心处处都是陷阱(第1页)
娶个亲还被人拦路喊冤,之前看过的小说里好像也没有这种戏码。
但是现在,这种意外它偏偏发生了。
而且,还发生在自己带着太子侧妃回毓庆宫的时候。
如果说这群拦路喊冤的太学生没有人组织,纯。。。
三日后,太子沈承率随行官员自京城启程,沿大运河南下,直赴江南。随行者除顾文昭外,尚有兵部尚书之子、户部侍郎之侄、御史台一名副使,皆为朝廷重臣子弟,意在监察新政推行之实情,亦为太子之臂膀。
一路南行,太子仪仗浩荡,沿途州府皆设行辕,备极尊崇。然沈承并未因身份显赫而懈怠,每至一地,必亲自召见地方官员,细查新政施行之效。顾文昭亦未闲着,暗中联络旧识,探查江南士族残余势力之蛛丝马迹。
江南之地,水网密布,商贾云集,自古繁华。然自新政推行以来,土地兼并之风稍抑,赋税之制更趋公平,百姓虽有怨言,然大体尚可维系。唯士族旧门,多有不满,暗中串联,图谋复起。
太子南巡至苏州时,忽接京中密报,言三皇子沈奕虽被禁足于府,然其门客暗中奔走,竟与五皇子沈恪有所勾连。五皇子素来低调,行事谨慎,然其母妃乃前朝旧族之后,与江南士族颇有渊源。此番联络,恐非偶然。
沈承阅罢密报,神色凝重。他知五弟沈恪素来隐忍,若真与三弟联手,朝局恐将生变。然他亦不敢轻举妄动,遂召顾文昭密议。
“顾大人,你可知五皇子与三弟之间,是否真有往来?”沈承低声问道。
顾文昭沉吟片刻,答道:“殿下,五皇子行事隐秘,微臣虽曾听闻些许风声,然未有确凿证据。若贸然上奏,恐反被陛下责问。”
沈承点头,沉声道:“朕亦知此事需谨慎。然若任其发展,恐将来难以收拾。”
顾文昭目光微闪,低声道:“殿下,若欲查实此事,或许可借江南士族之手。”
沈承眉头一挑:“哦?此话怎讲?”
顾文昭缓缓道:“江南士族之中,有一人极受五皇子信任,名为林世昌。此人原为五皇子府中幕僚,后因新政之故,被贬为庶人,然其仍与五皇子暗中书信往来。若能设法诱其现身,或可探得一二。”
沈承沉思片刻,缓缓点头:“好,此事便交由你去办。但切记,不可打草惊蛇。”
顾文昭拱手应命:“微臣明白。”
数日后,顾文昭借故南下吴县,暗中布置,果然引得林世昌现身。林世昌以为顾文昭仍为江南士族旧友,未曾防备,竟在密谈中透露五皇子与三皇子之密谋:二人欲借江南士族之力,联合朝中旧臣,于太子南巡之际,掀起一场风波,逼迫陛下动摇储君之位。
顾文昭将此事密报太子,沈承阅后,面色沉冷。他知此事若属实,陛下必震怒,然若贸然回京,恐反被五皇子等人抢先一步,反咬一口。思忖再三,他决定暂缓归期,先将江南士族残余势力彻底铲除,以绝后患。
于是,太子下令,命顾文昭协同地方官员,对江南士族中仍存旧势者展开清查。一时间,苏州、杭州、常州等地皆有士族被抄家查办,多名士族子弟被拘押,林世昌亦被擒获,供出五皇子与三皇子密谋之详情。
沈承将此事整理成奏章,命快马加急送至京中。
京中,沈昱接报后,脸色阴沉。他本以为三皇子之事已了,未曾想五皇子竟也牵涉其中。更令他愤怒的是,五皇子竟敢与三皇子联手,意图动摇储君之位,实属大逆。
他当即召见兵部尚书与御史台主事,命其彻查五皇子府。
五皇子沈恪被召入宫中,跪于御书房前,神色平静,毫无惧意。
“你可知罪?”沈昱冷冷问道。
沈恪抬头,目光坚定:“儿臣不知何罪。”
沈昱怒极反笑:“你与三皇子密谋,欲动摇储君之位,此等大逆之罪,你还敢说不知?”
沈恪缓缓道:“陛下,儿臣所做,皆为大晟江山。太子独揽大权,朝堂之上,皆为其党羽。若不加以制衡,大晟迟早落入其手中。”
沈昱目光一沉:“你这是在为自己的野心开脱?”
沈恪毫不退让:“儿臣不敢。但儿臣心中,始终以社稷为重。若陛下不信,可查我所做一切,皆为大晟计。”
沈昱沉默良久,最终缓缓道:“你与三皇子,皆被禁足于府中。朕将亲自审问,若有证据确凿,朕绝不轻饶。”
沈恪被押回府中,而沈昱则彻夜未眠。
翌日,他召见太子沈承之奏章,心中却愈发沉重。他知道,九位皇子皆非善类,而这场夺嫡之争,已无法避免。
与此同时,太子沈承在江南的清查行动,已彻底震动江南士族。许多旧族纷纷上书,请求朝廷宽恕,愿归顺新政。太子亦借机安抚民心,命地方官员重新厘定赋税,减免部分苛捐杂税,以示新政之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