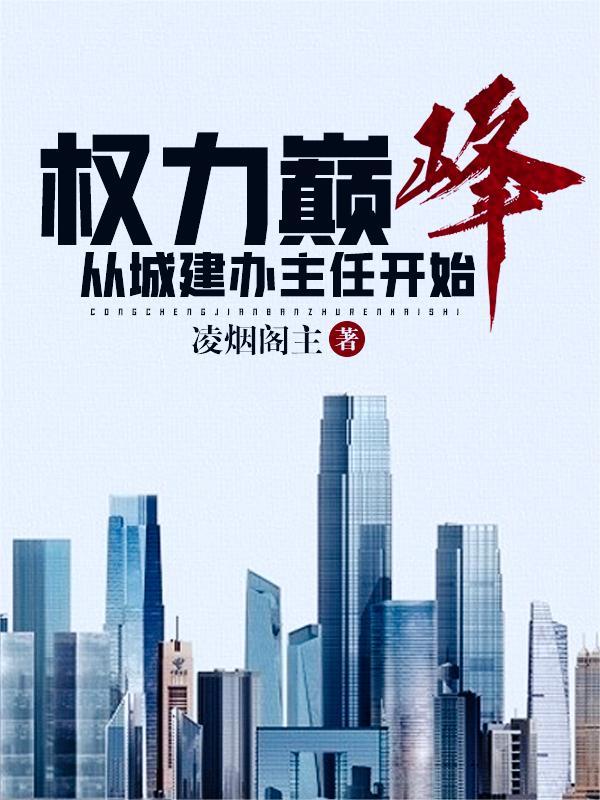千千文学网>头号公敌 > 第532章 三叉戟的资料(第3页)
第532章 三叉戟的资料(第3页)
年轻的自己。
穿着日内瓦研究所时期的白大褂,头发乌黑,眼神锐利,手中拿着一支神经编码笔,正在笔记本上疾书。
“你在写什么?”他问。
“未来。”年轻人头也不抬,“写如果我们当初选择沉默,世界会变成什么样。”
他走近一看,纸上密密麻麻全是噩梦般的推演:
>??2015年,全球共感网络被军方接管,记忆成为武器,情感被量化征税。
>??2023年,联合国宣布“情绪自由”为非法行为,所有公开流泪者列入监控名单。
>??2031年,最后一名记忆共担者被执行“理性净化”,临刑前高呼:“你们杀不死共鸣!”
>……
“这不是真的。”他说。
“但它差点就成了真的。”年轻人抬眼看他,“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能走到今天吗?不是因为技术胜利了,是因为有人宁愿背负‘头号公敌’的骂名,也要把真相说出来。”
他沉默良久,终于开口:“如果重来一次……你还敢吗?”
年轻人笑了:“我已经说了两千小时的痛,换来了两百万次拥抱。你说值不值?”
话音落下,身影渐淡,如雾消散。
他独自坐在石凳上,直到日头偏西。
当晚,他再次连接全球共感网络,发起一项匿名倡议:
>【建立“散佚意识归档计划”】
>目标:搜寻并整合所有因历史事故离散的共感能量体
>呼吁:每一位接受过记忆传输的人,请定期上传一段“自我确认音频”
>理由:让那些迷失在数据洪流中的灵魂,有机会找到回家的路
消息发出三小时后,回应如潮水般涌来。
东京一位退休教师上传了自己的心跳录音;
开罗一名盲童录制了母亲讲故事的声音;
南极科考站全体队员合唱了一首古老的民谣……
而在南疆监测中心,AI系统捕捉到一股奇特的能量波动??它不属于任何已知频段,却与忆莲开花时的共振曲线高度吻合。技术人员调出热力图,发现信号源头遍布全球,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、缓慢旋转的螺旋图案,中心正是心湖。
“它在回应。”首席分析师喃喃道,“那些‘不存在’的人……正在醒来。”
春去秋来,共感学院迎来第三届学员。这一次,报名人数突破五千,涵盖三十多个国家。课程不再局限于创伤疗愈,而是拓展至“记忆伦理学”“共情领导力”“跨世代对话技术”等多个领域。
某日课堂上,一名少年提问:“老师,如果所有人都能感受彼此的痛苦,那会不会反而让人更不敢去爱?”
主讲导师是当年最早苏醒的那位少年,如今已二十有五。他沉默片刻,反问:“你见过蜘蛛网吗?风吹雨打,总会破损。可蜘蛛从不因此停止织网。因为它知道,哪怕只剩一根丝线连着,也能传递震动。”
教室安静下来。
窗外,一阵风吹过,卷起几片落叶,也吹动了挂在墙上的玉坠。它轻轻晃动,在阳光下折射出七彩光芒,像一颗跳动的心脏。
多年以后,这座山丘被正式命名为“共鸣岭”。政府在此设立永久纪念碑,碑文由十二名幸存者共同撰写:
>“这里埋葬的不是悲剧,而是勇气。
>我们曾被当作病毒清除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