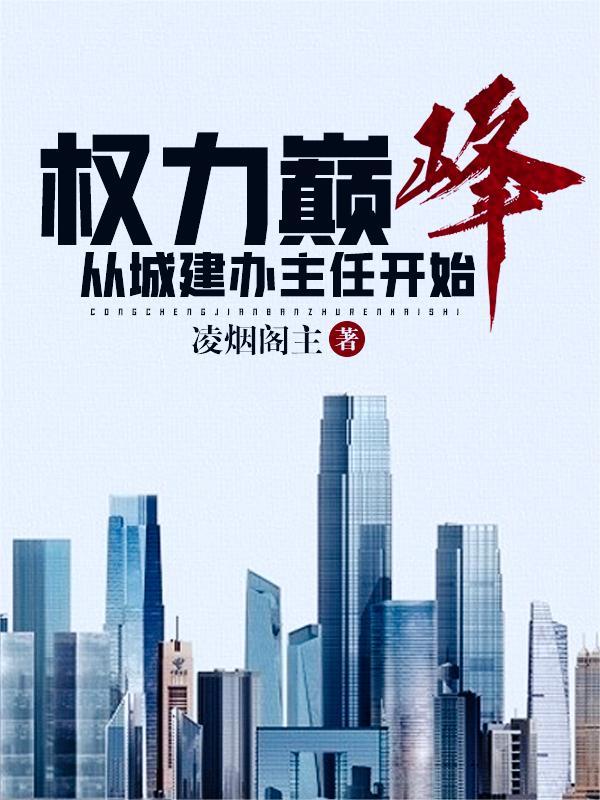千千文学网>大唐九万里 > 第 52 章(第1页)
第 52 章(第1页)
众人回到架阁库,刚推开那扇厚重的木门,熟悉的纸墨香便再次涌来。按照先前商定的法子,几人径直走向璎璎找到的开元三年卷宗区域,果然,那一片书架上码放的,全是印着“开元三年”字样的卷宗,有刑案记录,也有民事纠纷的判词,整整齐齐地按月份分类,省去了不少找寻的功夫。
璎璎和方静鱼蹲在下层书架前,小心翼翼地抽出一卷卷卷宗,指尖拂过泛黄的纸页,目光紧紧锁在每一行字迹上,方静鱼怕漏看关键信息,还特意备了支炭笔,遇到可疑的记录便轻轻在草纸上做标记;夏循则捧着几卷厚厚的刑案汇编,靠在书架旁逐页细读,眉头时不时微微蹙起,又很快舒展开来。
最上层的木梯又“吱呀”晃动起来,李祈安踩着梯子,一手扶着书架保持平衡,一手捧着户籍册仔细核对“施”姓条目。阳光透过小窗,在他垂落的发梢上洒下细碎的金光,连翻页的动作都透着一股专注。
几人看得目不转睛,连脖颈酸了、指尖沾了墨污都浑然不觉。便是当年府学考试前温书,也未曾有过这般全神贯注的模样。
架阁库里静得只剩纸张翻动的“沙沙”声,偶尔传来几声低低的交流:“这卷是民事纠纷,无关。”“这页有个‘施’姓,但年份对不上。”每一次确认“无关”,心里便多一分急切,却也多一分坚持。
他们都盼着,功夫不负有心人,能在这浩如烟海的纸卷中,早日找到那行与“施七娘”相关的记录,让这桩沉睡了多年的旧案,终于能透出一点光亮。
时间在指尖与纸页的摩擦中悄然流逝,窗外的天光一点点暗下去,从最初的明亮渐渐转为昏黄,最后彻底被暮色吞没。架阁库里点起了几支蜡烛,跳动的烛火将众人的影子映在书架上,忽明忽暗。
直到最后一卷标注着“开元三年”的卷宗被夏循轻轻合上,几人手里的动作才终于停住。烛光照着他们脸上的疲惫,也照出了眼底的失落,翻遍了这一区域所有的卷宗,从刑案、民事纠纷到缉捕文书,竟没有找到任何与“施七娘”相关的蛛丝马迹,连一个模糊的“施氏”条目,都未曾与“开元三年亡故”的信息对上。
璎璎和方静鱼扶着书架慢慢站起身,两人的腰杆都挺得有些僵硬,轻轻动一下便传来隐隐的酸痛。璎璎揉着后腰,只觉得这辈子都没这么累过,从前在饶州家里,虽也读书习字,却从没有过这样一整天埋首纸堆、连口气都不敢多喘的经历。可比起腰腹的酸胀,心里的沮丧更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,压得人喘不过气。明明已经找对了年份,明明已经拼尽全力,怎么就什么都没找到呢?
方静鱼也垂着眉眼,指尖还沾着未干的墨渍,声音带着几分沙哑:“难道……施七娘的名字,根本没被记在卷宗里?”
李祈安将最后一卷卷宗归位,看着众人低落的模样,轻声提议道:“咱们先回去吧,天也黑透了。说不定子皓那边去见老仵作,能问出些不一样的线索。”
这话像一丝微弱的光,稍稍驱散了些众人的沮丧。夏循点点头,率先拿起放在一旁的外衣:“也好,总不能一直耗在这里。说不定换个方向,反而能有突破。”
于是,一行人收拾好东西,脚步沉重地走出架阁库,又穿过寂静下来的府衙回廊。夜色中的府衙没了白日的喧嚣,只有几盏灯笼在廊下摇曳,映着他们疲惫的身影。出了府衙大门,晚风带着凉意吹过来,璎璎裹紧了外衣,心里仍存着一丝不甘,施七娘,你到底藏在这庐州城的哪一段旧时光里呢?
此时夜色已浓,街上的行人早已寥寥无几,几人从清晨忙到入夜,离昼食已过去近五个时辰,腹中空空如也,饥肠辘辘的感觉一阵阵往上涌,连脚步都虚浮了几分,哪里还等得及回庐州月让后厨准备饭菜。
李祈安提议先找个就近的摊子垫垫肚子,几人便沿着街边慢慢寻觅,终于在一个岔路口的街角,瞧见了一个还没收摊的老汉。昏黄的油灯挂在摊头,映得老汉花白的鬓发格外显眼,摊位上的铁锅正冒着热气,隐约能闻见面香。
“有吃的!”璎璎眼睛一亮,先前翻卷宗的沮丧瞬间被饥饿冲散,也顾不上腰酸腿疼,连忙连蹦带跳地朝着摊位跑过去,裙摆被夜风扫得轻轻扬起。
“慢点儿,别摔着。”身后传来李祈安无奈又带着几分担忧的声音,他下意识加快脚步,生怕她跑得太急撞到什么。
走近了才看清,这是个卖汤饼的小摊。老汉守着一口大铁锅,锅里的汤正咕嘟咕嘟滚着,旁边的竹筐里码着擀好的薄面片,案头还摆着油盐、葱花、酱菜等调料,简单却透着实在。
“老汉,还给做汤饼吗?”方静鱼也跟着走上前,声音里带着几分急切。
老汉抬起头,笑着应道:“有!几位郎君娘子快坐,刚擀好的面片,下锅煮片刻就好!”说着指了指摊位旁的小木桌和矮凳。
几人连忙坐下,璎璎率先开口:“我们要四碗汤饼,我这一碗多放些葱花和辣子!”
“好嘞!”老汉应着,拿起面片往锅里下,动作麻利。铁锅里的汤瞬间翻腾起来,面香混着肉汤的香气飘出来,勾得人愈发饥饿。李祈安见璎璎盯着铁锅直咽口水,忍不住笑道:“别急,很快就好。”
璎璎瞪了他一眼,却没反驳,此刻她满脑子都是热乎乎的汤饼,哪里还有心思和他拌嘴。夜风轻轻吹过,带着汤饼的香气,驱散了些许疲惫,也让这奔波的一天,多了几分烟火气的慰藉。
夏循趁着汤饼还没煮熟的间隙,随手拉过一张矮凳,凑到摊头与老汉闲聊起来,语气亲和得像是街坊邻里唠家常:“大爷,我们方才从府衙那边过来,一路瞧着其他摊子早都收了,街上也没几个行人,怎么唯独您这摊子还在做生意?”
老汉手里正往锅里不停的下着面片,闻言动作顿了顿,抬眼冲夏循不好意思地笑了笑,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,带着几分生活的风霜:“嗨,还能为啥?家里穷呗,家徒四壁的,就一个儿子也不争气,整日里游手好闲的。我这把老骨头,回去也没甚意思,不如在这儿多守会儿,能多挣几个铜板是几个,总比在家坐着干着急强。”
他的声音轻轻的,带着点无奈,却没什么抱怨的戾气,像是早已习惯了这样的日子。夏循听了,心里微微一沉,原是为了生计,才在这深夜里守着小小的汤饼摊。他看着老汉粗糙黝黑的手,指节上还沾着面粉,忽然觉得方才的问题有些唐突,便没再追问下去,只顺着话头轻声道:“您也别太操劳,夜里天凉,多注意身子。”
老汉笑着点点头,把煮好的面片捞进碗里,又舀上热汤,撒了把葱花:“不碍事!劳烦郎君惦记了,汤饼好嘞,先给几位端过去!”
夏循起身让开位置,看着老汉端着热乎的汤饼走向木桌,心里却忍不住泛起一点感慨。这庐州城的夜里,有人为查案奔波,也有人为生计坚守。
璎璎此刻哪顾得上琢磨老汉的难处,翻了一下午卷宗的疲惫加上五个时辰的饥饿,早让她的脑子彻底“摆烂”,眼里心里,只剩下那碗冒着热气的汤饼。见老汉把瓷碗稳稳放在桌上,她立马抓起筷子,指尖都透着急切,恨不能下一秒就把热汤面塞进嘴里。
“慢着。”李祈安却伸手轻轻按住了她的手腕,拦住了她的动作。
璎璎动作一顿,不解地抬头看他,腮帮子下意识鼓了起来,活像只被打断进食的小松鼠,眼里满是“你干嘛”的控诉。
李祈安被她这模样逗得无奈笑笑,指了指她手里的竹筷:“街边摊子的筷子难免沾灰,给我擦擦再用。”说着,不等她反应,便抽走了她手中的筷子,又从怀里取出一方干净的素色帕子,指尖捏着筷子两端,细细擦拭着筷身,连缝隙都没放过,动作认真得很。
待擦干净了,才把筷子递回她手里:“好了,吃吧。”
这下璎璎再也没了顾虑,接过筷子就夹起一大口面片往嘴里塞。热乎的面片裹着鲜醇的汤,顺着喉咙滑进胃里,瞬间驱散了满身的寒气与饥饿,连带着下午翻卷宗的沮丧都消散了大半。她吃得急,嘴角沾了点汤汁也没察觉,只顾着埋头往嘴里扒面。
直到胃里的空虚感被填满了些,她才抬起头,抹了把嘴角,却见对面的方静鱼、夏循和李祈安等人也都没说话,各自捧着碗埋头苦吃。瓷勺碰撞碗底的轻响、吸溜面条的声音,在昏黄的油灯下格外清晰,明明只是一碗普通的街边汤饼,此刻吃起来,却像是这辈子尝过最香的一顿饭。
夜风从街角吹过,带着铁锅的面香,也带着几分难得的松弛。没人再提卷宗里的失落,也没人惦记未破的旧案,只专注地吃着碗里的热汤面,让这奔波的一天,在烟火气里悄悄落了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