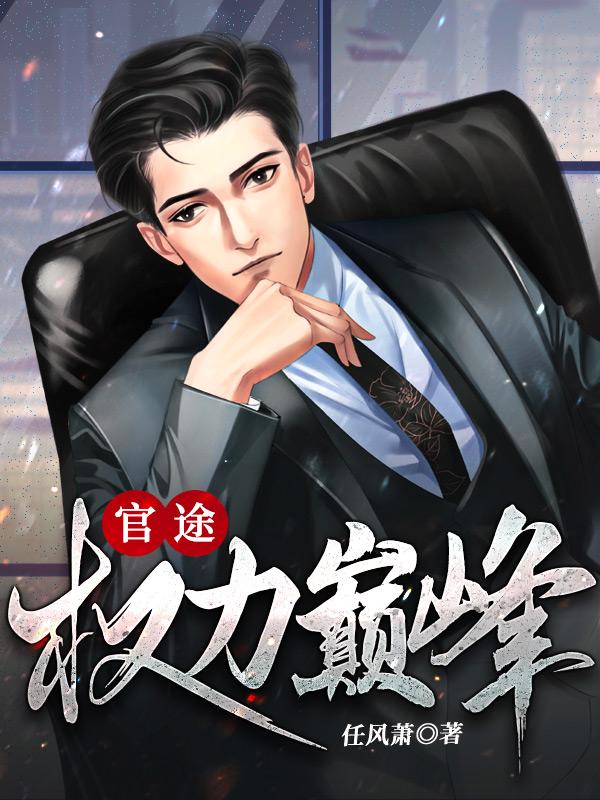千千文学网>替嫁植物人?她靠医术飒爆了 > 第311章(第2页)
第311章(第2页)
那座工匠之城的改造案在国际文化界曾引起过巨大的争议,被许多人抨击为“资本对文化的无情绞杀”。
但在场的商人们只看到了其巨大的商业成功,从未有人敢在罗威尔的总裁面前,如此赤裸裸地揭开这块遮羞布。
场内,那几位被邀请来的文化界泰斗和艺术评论家,脸色瞬间变得无比凝重。他们看向克劳斯的眼神,已经带上了审视与怀疑。
戚长信脸上那份运筹帷幄的从容,第一次消失了。他死死地盯着台上的沈言安,眼神里充满了惊骇与难以置信。
他算到了一切。算到了戚文燕的贪婪,算到了九处的介入时机,算到了沈言安会反击,甚至算到了她可能会在艺术性上做文章。
但他唯独没有算到,这个女人竟然能完全跳出商业竞标的棋盘,从文化哲学的高度,从一个他自认为最无懈可击的地方,对他进行反击。
某种意义上,这是诡辩。
但坏就坏在……罗威尔集团有前科!
克劳斯那张万年不变的冰山脸上,第一次出现了明显的情绪波动。他站在那里,面对着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,陷入了长达十几秒的沉默。
在无数镜头的注视下,这十几秒的沉默,本身就是一种溃败。
他精心准备的所有商业说辞,在这一记灵魂拷问面前,都显得如此苍白无力。
最终,他还是给出了一个标准的外交辞令:“罗威尔集团一向尊重并致力于推动全球化的文化融合,我们会……”
那些空洞的词汇,在沈言安刚才那番尖锐质问的映衬下,显得格外虚伪和敷衍,反而加深了众人的疑虑。
场内的舆论彻底分裂了。
商人们依旧坚信资本的力量,认为罗威尔的方案无可替代。
但官方代表、文化界的专家们,却已经陷入了激烈的争论。
沈言安以一人之力,强行改变了这场竞标的评判标准。
在经历了漫长而压抑的讨论后,那位官方负责人终于面色凝重地重新登上了高台。他拿着话筒的手,似乎有千斤重。
整个宴会厅再次安静下来,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
负责人艰难地清了清嗓子,目光复杂地看了一眼台下的沈言安,最终宣布了结果。
“经过项目组的综合考量……本次城北地块竞标的最终获胜方是,戚长信先生。”
结果宣布的瞬间,场内响起一片无法抑制的叹息声。
尽管沈言安赢得了道义和人心,但在那庞大到足以影响城市经济格局的资本实力面前,官方最终还是做出了最现实、最稳妥的选择。
面对这个结果,沈言安和黎妄的脸上,却没有丝毫的失落。
两人对视一眼,看到了彼此眼中的默契与了然。
输掉一个项目,却赢得了对手的敬畏,赢得了人心向背。